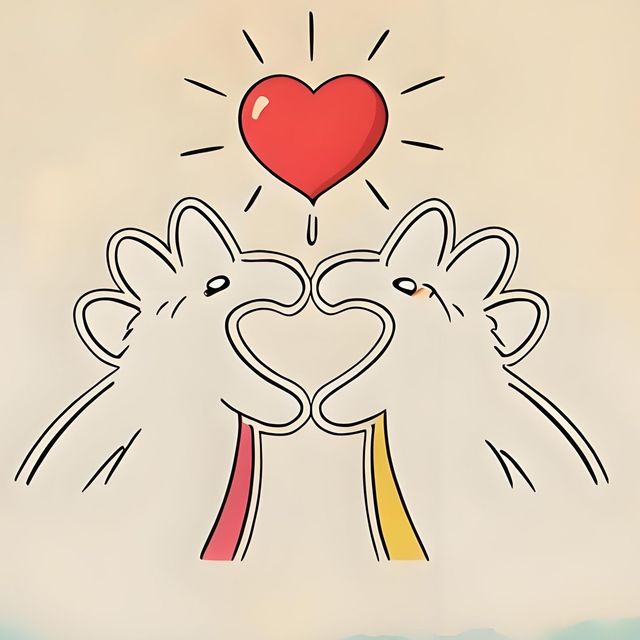离开乔城的那天,晨露还凝在马鞍上。比彘挑着两只竹筐走在前面,左边装着染坊老匠给的花籽,右边是小乔连夜缝制的虎头鞋,念安坐在筐沿,小手揪着他肩头的补丁,咿咿呀呀数着路边的野菊。
博崖的风带着草木香,吹得竹屋前的老玉兰沙沙响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蛛网在梁上结了层薄纱,去年晒的草药还在窗台上,只是干得像脆纸。比彘放下担子就去劈柴,斧头起落间,惊飞了檐下做窝的燕子——它们倒也不认生,盘旋两圈又落回原位,仿佛知道这里的主人回来了。
修缮竹屋的日子总被念安的笑声填满。比彘给屋顶换茅草时,孩子就坐在门槛上,把碎草往他头发里扔;我糊窗纸时,他又拽着纸角晃悠,害得浆糊蹭了满衣襟。有天傍晚,比彘突然从后山扛回块青石板,凿成方方正正的灶台:“以后煮肉不用蹲在地上了。”石板边缘还留着他凿出的小坑,说是给念安放木勺用的。
开垦荒地那天,比彘给念安做了把小锄头,木柄被砂纸磨得溜光。孩子攥着锄头跟在后面,在翻松的泥土里踩出一串串小脚印,突然蹲下身抓起只蚯蚓,举到比彘面前咯咯笑。他慌忙丢下锄头去抢,怕那软乎乎的东西吓着孩子,却被念安的小手按在掌心:“虫,爬爬。”
我在屋前种了片秋葵,刚冒出嫩芽就被念安揪着玩。比彘索性在旁边圈出块小地,撒上乔家带来的菜籽:“让他自己种,看还舍得揪不。”果然,孩子每天蹲在地里,用小水壶给嫩芽浇水,裤脚沾着泥也不肯换,夜里还抱着水壶睡,生怕被露水打湿了他的“宝贝”。
竹屋旁的溪流被比彘砌了道小坝,积水成潭,正好能浣纱。我把乔家送的靛蓝草泡在潭里,念安就光着脚丫在岸边踩水,看布帛在水里慢慢变蓝。比彘坐在潭边削木盆,木屑飘在水面上,像撒了把碎银。“冬天可以在这里凿冰捕鱼,”他突然转头冲我笑,鬓角的白发被夕阳染成金红,“去年藏的鱼篓还在柴房呢。”
有回暴雨冲垮了屋后的篱笆,比彘带着念安去修补。孩子递藤条时总往反方向递,惹得比彘直笑,却还是耐着性子教:“要像编筐一样,一上一下才结实。”等篱笆重立起来,念安的小手被藤条勒出红痕,却举着自己编的小藤圈跑来炫耀,圈里还放着朵野蔷薇。
夜里躺在新铺的竹席上,听着窗外的虫鸣,念安的小呼噜声混在其中,像支温柔的曲子。比彘的手搭在我腰间,掌心的茧子蹭过我的衣襟——那是常年握刀、劈柴、耕地磨出的,却比任何锦缎都让人安心。“你看这星星,”他突然指着天窗,“比乔城亮多了吧?”
念安的菜籽终于长出了小青菜,他非要摘下来炒着吃,结果炒出的菜梗比手指头还粗。可他吃得香,小油嘴蹭在比彘脸上,把胡子都染成了黄的。我看着父子俩笑作一团,突然觉得所谓幸福,不过是竹屋炊烟、田间稚语,是有人陪你把日子过成细水长流,连柴米油盐里,都藏着甜。
作者谢谢七位宝宝的花花
作者笔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