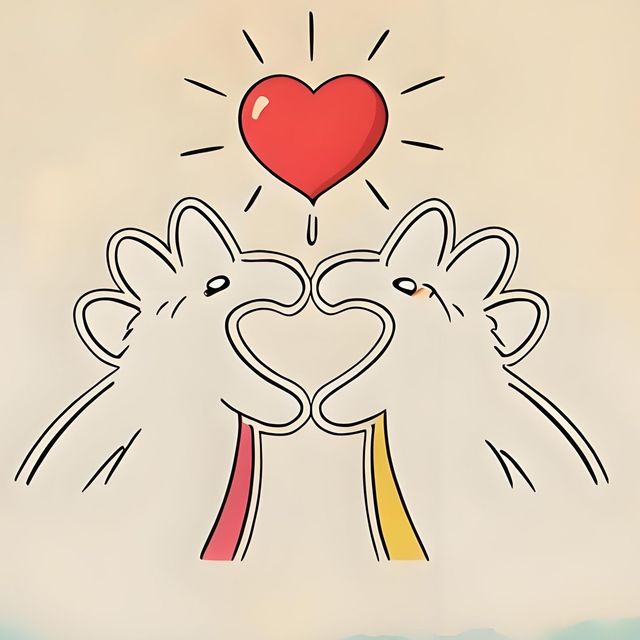竹屋的篱笆爬满牵牛花时,念安已经能背着半篓野果从山里跑回来了。
他教阿棠辨认毒草,说“这种紫色的不能碰,爹说沾了会起疹子”,阿棠就举着小竹篮跟在后面,把哥哥说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,遇到相似的草就拽着他的衣角喊“多多看!”。
比彘的背比从前弯了些,却还是习惯天不亮就进山。
只是不再追着野猪跑,更多时候是采些菌子、挖些草药,回来时总能带回支野蔷薇,往我鬓角一插:“比染坊的靛蓝花好看。”
他的手背上添了道新疤,是采崖柏时被石头划的,我给他上药时,他却笑:“这点伤算啥,当年在乔城被染缸砸了脚,还不是照样扛布?”
阿棠十岁那年,念安带着她在溪边设了陷阱,竟真的捕到只小野兔。孩子捧着兔子跑回来时,草鞋上全是泥,阿棠的布裙沾着草屑,却举着兔子耳朵喊:“娘你看!我们也会打猎了!”
比彘蹲在灶前烧火,闻言往灶膛里添了根柴:“兔子放了吧,它娘该找它了。”兄妹俩对视一眼,真的把兔子送回了草丛,回来时手里攥着把野草莓,说是“给娘赔罪”。
深秋晒谷时,念安已经能帮着比彘牵牛碾场了。木枷在谷穗上滚过,他吆喝牛的调子和比彘一模一样,只是声音更清亮些。
阿棠则坐在谷堆上翻晒玉米,小辫子上系着我新染的红头绳,时不时往哥哥嘴里塞颗炒栗子。比彘靠在槐树下抽烟斗,看着他们的眼神像被阳光晒过的蜜糖,黏糊糊的全是甜。
有年冬天特别冷,溪水结了层薄冰。
比彘把家里的旧棉袄拆了,重新絮上野棉花,给念安做了件新棉袍,又给阿棠缝了双棉鞋,鞋底纳得厚厚的,说是“踩在雪地里不冻脚”。
我坐在油灯下染布,他就坐在旁边劈柴,斧头起落间,突然说:“等开春,咱们把东头的荒地开出来,种点高粱,给孩子们做糖吃。”
念安十五岁那年,跟着魏劭去乔城学了半年账。回来时背回个大木箱,里面装着给阿棠的花布,给我的胭脂,给比彘的新烟袋。
他说在乔城看到新的染布法子,比咱们的省时三成,说着就蹲在院里画给我们看,竹枝在泥地上划出靛蓝草的模样,阿棠凑在旁边看,突然说:“哥哥画得不如娘染的好看。”
比彘的白发越来越多,却还是爱扛着锄头去菜地里转。
他教念安如何看墒情,说“土块捏起来能成团,落地能散开,这时候下种最好”,念安就蹲在旁边记,阿棠则把父亲的话编成顺口溜,“成团散,种不难,长出苗儿比人欢”,惹得比彘直笑:“这丫头,比你娘当年还会编。”
我染的布渐渐出了名,山外的货郎常来换,说“博崖的蓝布不褪色,做棉袄里子最好”。
比彘就把换来的红糖、细盐全留给孩子们,自己啃着玉米饼说“我糙惯了,吃啥都香”。有次货郎带来块西洋镜,能看到乔城的街景,阿棠趴在镜前看了半晌,突然说:“不如咱们的竹屋好看,没有爹种的紫苏。”
除夕夜,竹屋的油灯亮到后半夜。
念安贴的春联歪歪扭扭,却是用我染的红布剪的,阿棠在门框上挂了串野山楂,说是“比城里的灯笼红”。
比彘端来炖了整夜的鸡汤,陶罐里飘着当归的香,他给每个人碗里都舀了块鸡腿,自己却啃着鸡头,说“鸡头转得灵,来年打猎准能着”。
守岁时,念安说要在博崖盖间新屋,用青砖砌墙,比竹屋暖和。阿棠说要在院里种满染布的花草,蓝的、紫的、黄的,像彩虹落在院里。
比彘往我手里塞了个烤红薯,烫得人直搓手,他的掌心虽然布满老茧,却比任何时候都让人踏实:“盖啥新屋,这竹屋住了十几年,风风雨雨都挡得住,就像咱们一家人,挤着才暖和。”
窗外的雪落得轻悄,把竹篱上的牵牛花藤盖成了白色。阿棠靠在比彘膝头睡熟了,念安还在讲他听来的故事,说山外的人如何羡慕咱们的日子。
我望着比彘鬓角的霜,望着孩子们年轻的脸,突然觉得这幸福就像院角的老槐树,根在博崖的土里,枝桠伸向天上的星,春有花,夏有荫,秋有果,冬有雪,一年年,一代代,守着这竹屋,守着彼此,就这么慢慢长下去,长成岁月里最安稳的模样。
作者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