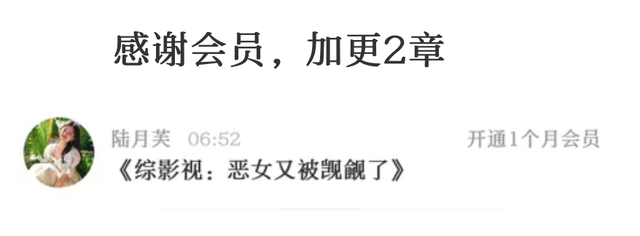-
当初他不知深浅,曾当着众人的面喊过一声“苏茯苓”,结果一道炽热箭风擦着他的耳廓飞过,烧焦了他鬓角的发,在他脸颊留下了一道细微的血痕,和她那句冷淡的警告。
自此,他对这女人的恐惧,深植心底。
苏昌河将谢千机的反应看在眼里,非但没有收敛,反而极其自然地伸出手臂,勾住了茯苓的肩膀,将她往自己怀里带了带,语气带着几分欠嗖嗖的调侃。
苏昌河瞧瞧,我们射魂师茯苓大人的名声,在暗河内外都这般好用。
苏昌河连谢兄这样的狠角色,见了你都怕得发抖。
他侧过头,几乎贴着茯苓的耳廓,温热的气息拂过,声音压低。
苏昌河说起来,你在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射魂师,在暗河内也是止小儿夜啼的存在。
苏昌河这名声,怎么比我这个送葬师还要臭上几分?
茯苓任由他勾着,并未推开。
他身上还带着方才打斗后未曾散尽的血腥气,混合着他本身那股阴郁危险的气息,扑面而来。
她抬起眼,目光清凌凌地扫过谢千机那副强自镇定的模样,最后落在苏昌河近在咫尺的脸上,唇角微微勾起一个没什么温度的弧度。
茯苓名声臭?
她语气轻缓,带着点玩味。
茯苓这个形容,在我看来倒像是褒义。
茯苓很是顺耳。
苏昌河闻言,低低笑了起来。
他喜欢她这般模样,对这世间评判标准的不屑一顾,与他如出一辙。
苏昌河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
他揽着她的手收紧了些,像是宣告所有权般,看向面色更加苍白的谢千机。
苏昌河谢兄,戏看完了,伤也受了,还不回去禀报?
谢千机如蒙大赦,不敢再看茯苓,强忍着伤痛,对苏昌河匆匆拱了拱手,带着那尸体,身形有些踉跄地迅速消失在巷道尽头。
巷道内只剩下他们两人。
苏昌河这才松开茯苓,微微弯腰靠近,和她面对面。
苏昌河如何?这出戏可还精彩?
他抬头看她,眼神亮得惊人,像是在等待夸奖。
茯苓目光扫过地上的尸体,又落回他写满野心与亢奋的脸上。
茯苓谢家老的,你想借刀杀了。
茯苓大家长,你也要杀。
茯苓苏昌河,你撺掇这么多人,是想把暗河的天彻底掀过来?
苏昌河直起身,与她对视,嘴角噙着笑,那笑容里再无半分平日伪装出的滑头或惫懒,只剩下赤裸裸的狂妄与志在必得。
苏昌河旧的天黑了太久,也该换片新的了。
苏昌河茯苓,这潭死水底下埋着太多腐肉,不挖干净,如何新生?
他向她伸出手,掌心向上,沾染过血迹的手指修长而骨节分明,在夜色中仿佛带着某种蛊惑。
苏昌河要不要和我一起?
苏昌河把这天,捅个窟窿出来。
茯苓看着他伸出的手,没有立刻回应。
夜风吹拂起她鬓边的发丝,拂过她冷艳的侧脸。
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