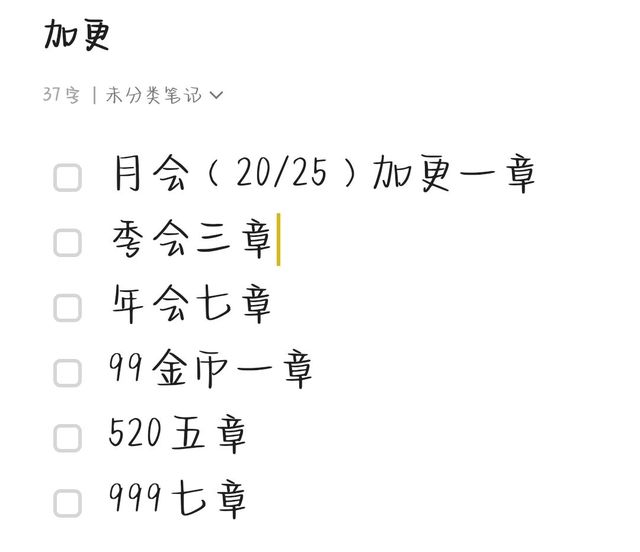苏昌河靠在梨花木椅上,背脊微弓,让慕飞霜能舒服地窝在他怀里。
她的发梢还带着白日里山间水汽的清润,蹭过他的下颌时,痒得他指尖都软了几分。
他垂眸看着怀中人,她正盯着桌案上跳动的烛火,睫毛在眼下投出细碎的影,像两片停驻的蝶翼,连呼吸都轻得怕惊散了这夜的静。
窗外忽然掠过一道灰影,带起极淡的翅风。
慕飞霜先动了,指尖刚触到苏昌河的手腕,便借着他的力道轻轻起身,裙摆扫过椅腿时,绣着的兰草纹样在烛火下晃了晃。
那是只信鸽,羽色是极干净的白,唯有尾尖沾了点夜露的湿,正歪着头用尖喙轻轻啄着窗纱,腿上绑着的信封是浅青色的,还印着半朵白鹤纹。
是南安城白鹤药庄的标记。
慕飞霜指尖捻住信鸽的脚环,动作轻得怕弄疼了它,信鸽倒也乖,蹭了蹭她的指腹,才振翅飞向院中的老槐树。
她拆开信封时,指腹触到信纸的质感,是南安城特有的竹浆纸,带着点淡淡的竹香,上面的字迹是小神医白鹤淮特有的,笔锋偏软,却又在转折处透着股少年人的利落。
苏昌河“笑什么?”
苏昌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带着刚起身的慵懒,他原本仰躺在床边,手肘撑着枕,手掌托着脑袋,目光落在慕飞霜的侧影上。
烛火把她的轮廓描得暖融融的,连拆信时微微抿起的唇,都显得软乎乎的。
他太了解她了,寻常邀约绝不会让她露出这样的笑,那笑意里藏着点狡黠,像只偷了糖的猫。
慕飞霜把信纸折了折,攥在手心转身,故意把笑容压了压,却还是没藏住眼底的亮
慕飞霜“咳咳,没什么,鹤淮说南安城近来樱花开得好,让我们去玩几天。”
她说着,还往后退了半步,靠在窗台上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信纸边缘。
苏昌河挑了挑眉,从床上起身时,玄色外袍滑落肩头,露出里面素色的中衣,他步子迈得慢,却带着股不容躲闪的气势
苏昌河“哦?她会这么好心?”
话音未落,他已经伸手去夺她手里的信。
他太清楚慕飞霜的小动作了,越是藏着掖着,越说明信里有猫腻。
慕飞霜“哎,你别抢!”
慕飞霜往后一躲,后腰却猛地撞上了靠墙的木桌,桌面上传来“叮”的一声轻响,是下午没收拾的茶盏碰在了一起。
她还没来得及站稳,苏昌河已经贴了上来,胸膛紧紧抵着她的后背,他的呼吸带着刚从暖被里出来的温度,落在她的耳后,烫得她耳尖瞬间就红了。
木桌的凉意透过薄薄的衣料渗进来,和身前男人的温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慕飞霜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手掌搭在桌沿时的力度,指节微微泛白,连呼吸都比刚才急促了些。
他总是这样,看似吊儿郎当,可一旦靠得近了,耳根子比谁都容易红。
她忽然转过身,借着桌面的支撑微微踮脚,右手轻轻捏住苏昌河的下巴,迫使他低头看着自己。
她的眼睛很亮,像盛着星子,映着烛火的光,连带着笑容都染上了几分计谋得逞的得意
慕飞霜“苏昌河,”
她故意拖长了语调,指尖轻轻蹭过他的下颌线
慕飞霜“原来令人闻风丧胆的暗河送葬师,也会有脸红害羞的时候啊?”
苏昌河的喉结动了动,目光落在她的唇上,看着那抹笑一点点扩大,竟真的晃了神。
可也就一瞬,他手腕一翻,指尖已经勾住了她攥着信纸的手,轻轻一扯,便把信夺了过来。
动作快得让慕飞霜都没反应过来。
慕飞霜“你!”
慕飞霜瞪着他,指尖还保持着捏下巴的姿势,气鼓鼓地跺脚
慕飞霜“不讲武德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