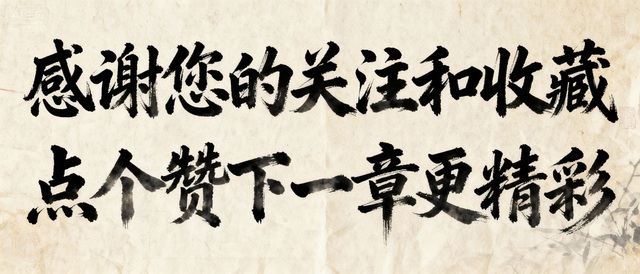我瘫在太师椅上,感觉整个人都快散架了个屁的了。胸口那片被“老毛子”拍中的地方火辣辣地疼啊,每一次呼吸都像拉着破风箱一样,还带着铁锈味儿。
王富贵那个老神棍,还把一坨黑乎乎、散发着浓郁草药和……呃,某种不可名状气味的膏药,糊在我胸口,恶心死了。
上官牧“嘶——我说王道长啊!您这玩意儿是疗伤还是要命啊?比刚才挨那一下还疼!”
我龇牙咧嘴地倒抽冷气。
王富贵“疼?”
听我这样说,这个王富贵手下力道半点不减,按得我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,王富贵“疼就对了!那家伙的掌力带着阴劲儿,专伤内腑。要不是你小子的身子骨被那‘房客’提前用杀气淬炼过,这会儿你胸骨早断了!现在只是淤血堵着,算你祖宗积德!”
苏柠就我在旁边站着,还举着她那租来的破平板,屏幕上的光映得她小脸煞白——嗯。她手指划拉着,嘴里念念有词:
苏柠“心率132,肾上腺激素水平超标,局部肌肉群轻微撕裂……意识波动频谱紊乱,双峰值对冲现象明显……”
我没好气地朝她翻了个白眼,虽然牵动了伤口又是一阵龇牙:
上官牧“废话!外面我刚跟十几号人玩过命,还得被你们师徒俩当猴儿看,对了,外加下注开盘,我能稳定就有鬼了!”
王富贵听后嘿嘿一笑,糊完膏药,居然从他那油腻的道袍袖子里摸出个扁银酒壶,自己美滋滋地抿了一口,然后还递到我面前:
王富贵“来一口?正宗虎骨酒,固本培元。”
看着那壶嘴上可疑的反光,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瞬间回忆起那颗“猫粑粑”仙丹的绝世风味,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:
上官牧“谢了您嘞!我还想多活几年!我说你到底是是老道还是博士啊!”
王富贵“哼!不识货,不喝拉倒,我是什么身份重要吗?”
王富贵撇撇嘴,收回酒壶,脸色倒是正经了几分。
王富贵“小子,别以为你就是走了背字。你这是蹚了‘阴墟’,所以成了‘锚点’!科学的尽头是玄学,玄学的手段是科学,你啥时候明白了这句话也就算出徒喽!”
上官牧“‘锚点’?”这词儿,我听着就透着不祥,不过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这话我还是认可的,要不然那么多大科学家最后咋都新神了呢,肯定是这样。
王富贵“简单说,你小子现在就是个不稳定的空间坐标!”
王富贵用沾着药膏的手指在桌上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圈,一着笔画这一边说:
王富贵“你看啊,这边,是咱们这旮沓。那边,是你梦里那个地方。而你呢?就是连着这俩圈的那根线!普通人做梦,神游太虚,去了也就去了。你这倒好,直接打了个钢桩下去,还把另一个世界的‘你’给硬生生栓过来了!”
苏柠适时地在平板上调出一个动画,给我演示了起来:两个扭曲的气泡被一根闪烁不定的光线连着,看着就让人头晕。
上官牧“那……那会咋样?”
我感觉喉咙发干,比刚才打架时还紧张。
王富贵“咋样?哼!”
王富贵冷笑一声,那声音像冰碴子刮过骨头:
王富贵“你这‘锚点’不稳,两个世界的规则在你身上打架。时间久了,轻则精神分裂,变成真疯子;重则‘锚点’崩溃,嘭——你这身皮囊就成了两个世界对撞的炮灰,最后死得连点儿渣都剩不下!”
上官牧“啊?”
看我惊讶他又顿了顿,用那双看似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我,像要看进我灵魂深处似的:
王富贵“更别提,你现在就是黑夜里的灯塔,肉包子打狗——不对,是肉包子引恶狼!就说想抓你的那个‘虎爷’和他背后的‘贵客’吧,他们盯上的恐怕不是你这条小命,而是想通过你这个‘锚点’,干点什么勾当!那些脑袋会自爆的杀手,就是明证!根本不是咱们这边的技术,但是已经出现好几起了!我都见怪不怪了!最近都是这破事儿!”
我靠!这信息量他妈的也太大了吧!我一直还以为就是我个人的倒霉催事儿,没想到已经上升到这个层面了?我此刻啊感觉自己的脑子嗡嗡的,比挨了十下闷棍还懵。
所以,我不能光想着把“香烟”那犊子给弄死或者赶走,还得……稳住这个局面?一想到这儿啊,我脑子里就乱成了一团麻。
上官牧“就是说,平行世界入侵是吗?”
王富贵“对喽!这小子还不笨嘿,总算是开了点窍了,你这个词儿用的还挺贴近,至于他们想干啥,那就得顺着你这条线儿好好捋捋了。”
王富贵此刻的语气才缓和了点,合着一直拿我当笨蛋呢啊?
看我似懂非懂的小眼神儿,他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欠揍的德行:
王富贵“所以嘛,特训是必须的。我不让你练拳脚,你脑袋里的那‘房客’留给你的本能就够你嚯嚯一阵子了。练的是这个——”说着,他伸出了根手指,重重地点在了我的眉心上。
王富贵“掌控你的‘神’,守住你的‘识海’!事儿呢,就问题不大了!”
果然啊接下来的几天就让我留在了这个道观里,他们对我开启了精神训练。
第一课,就在我这半信半疑、浑身疼痛的状态下开始了。
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一万倍,也他妈的痛苦一万倍。我被要求盘着腿坐在了个硬邦邦的蒲团上,闭上眼睛,努力啥也不想,就在脑子里盖一堵“墙”,他们说这叫“防火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