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0年3月17日,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橡木穹顶下,拉丁语的辩论声如同陈年羊皮卷般厚重压抑。
林砚站在质询委员会的长桌前,黑色学术袍的袖口被他攥得发皱,指尖的墨渍与古籍残页的纤维混在一起,那是他过去三个月在图书馆地下室钻研的证明——证明他所谓的“异端学说”并非空穴来风。
“林砚先生,你坚持认为墨家‘非攻’思想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存在文明互证,甚至断言墨家掌握着超越时代的机关学体系,这是否违背了历史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?”教务长阿诺德爵士推了推金丝眼镜,镜片后的目光如同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冰冷而傲慢。
林砚抬起头,这位年仅26岁的语言学天才,发际线已因过度思索而微微后移,但双眼却亮得惊人。他摊开随身携带的牛皮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古希腊语、梵语、古汉语的对照注释,还有手绘的几何图形。
“爵士,实证主义的核心是‘有证可依’,而非‘墨守成规’。”他的牛津腔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西域口音——那是童年跟随传教士父亲在敦煌生活时留下的印记,“我在《墨子·备城门》篇中发现了与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第三卷高度吻合的圆幂定理表述,比西方早了整整两百年。更重要的是,这段文字旁的鸟虫书批注,经我破译,涉及‘光影折射’‘力的平衡’等机关学原理,这绝非古代普通思想家所能企及。”
委员会成员们发出一阵低低的哗然。坐在角落的顾亭林教授眼中闪过一丝欣慰,却又迅速被忧虑取代。这位年近六旬的汉学泰斗,是林砚的恩师,也是唯一支持他研究墨家学说的学者。
三个月前,顾亭林以“西域考古调查”为名远赴中国,临行前曾私下告诫林砚:“墨家秘学牵涉甚广,有些真相,或许沉睡在历史中更为安全。”
但林砚彼时正沉浸在发现的狂喜中,并未深思恩师的警示。他继续说道:“更关键的证据在于这份敦煌出土的残绢——”他举起一份装在玻璃展柜中的文物复制品,绢帛上的鸟虫书扭曲如活物,“这是顾亭林教授临行前寄给我的,上面的符号系统结合了墨家逻辑与天文历法,我初步破译出‘非攻’‘巨城’‘罗布泊’等关键词。这证明墨家并非单纯的哲学流派,而是拥有实际工程能力的超文明群体。”
“一派胡言!”历史学教授布莱克伍德猛地拍案,“墨家早已在汉武帝时期消亡,所谓‘超文明’不过是东方主义的幻想!林砚先生,你被神秘主义冲昏了头脑,甚至公开质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,这是牛津大学绝不能容忍的异端行为!”
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,林砚凭借精湛的语言学功底、缜密的逻辑推理,一次次驳倒委员会的质疑。但他渐渐发现,这场听证会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探讨,而是一场预设结局的审判。
当阿诺德爵士最终念出“开除学籍,终身禁止进入牛津学术圈”的判决时,林砚没有辩解,只是默默收起了笔记本。
走出博德利图书馆时,伦敦的冷雨正淅淅沥沥地下着。学术圈的朋友们避之不及,昔日的同窗纷纷绕道而行,唯有顾亭林教授的助手送来一个密封的木箱,里面是恩师留下的所有墨家相关手稿,还有一张字条:“敦煌藏秘,墨者未绝,慎之。”
林砚回到租住的旧书店阁楼,这里堆满了他搜集的古籍珍本。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,三天三夜不眠不休,重新梳理顾亭林留下的手稿。
在一本《敦煌杂抄》的夹层中,他发现了半张残破的绢帛,与听证会展示的复制品恰好拼接完整。绢帛上的鸟虫书经他再次破译,又多出“止战”“机关”“逃墨”四字。
“逃墨……是逃离墨家,还是墨家在逃亡?”林砚喃喃自语,指尖划过绢帛上的几何符号。
这些符号排列奇特,既非传统的八卦,也非西域的占星图。他突然想起《墨子·经说下》中的记载:“景到,在午有端,与景长。说在端。”
这是墨家光学中关于小孔成像的论述。林砚立刻找来一张白纸,用蜡烛模拟光源,将绢帛放在中间,果然在纸上投射出一串扭曲的线条——那是一幅简易的地图轮廓,隐约可见“敦煌”“藏经洞”的字样。
就在这时,阁楼的电报机突然急促地响起,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林砚冲过去,纸带缓缓打出两个字,墨迹未干,却带着穿透时空的紧迫感:“逃墨。——顾亭林”
没有地址,没有署名,只有这两个字,与绢帛上的破译结果不谋而合。林砚的心猛地一沉,他立刻查阅最近的报纸,发现三个月前顾亭林抵达敦煌后,曾在《泰晤士报》发表过一篇关于藏经洞考古的短文,此后便杳无音讯。
最后一条相关消息来自一位英国探险家,他在信中提到“敦煌附近有黑衣僧人活动,行踪诡秘,似在寻找某物”。

林砚点燃一支烟,目光落在窗外的雨幕中。牛津的除名、恩师的失踪、神秘的绢帛、诡异的电报,所有线索都指向遥远的中国西域。
他知道,自己必须去敦煌,不仅是为了洗刷“异端”的污名,更是为了揭开墨家秘学的真相,找到失踪的恩师。
第二天清晨,林砚将所有古籍珍本变卖,换取了前往中国的船票。
当他登上前往苏伊士运河的轮船时,口袋里揣着那半张绢帛和电报纸带,脑海中回荡着顾亭林手稿中的一句话:“墨家之秘,不在典籍,而在人心;非攻之术,非为止战,实为逆天。”
船行至红海时,林砚遭遇了第一次危机。两名西装革履的男子突然闯入他的船舱,自称是牛津大学的“学术调查员”,要求他交出顾亭林留下的手稿。
林砚一眼识破对方的谎言——他们的皮鞋上沾有中东地区特有的沙漠红土,袖口的纽扣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专用样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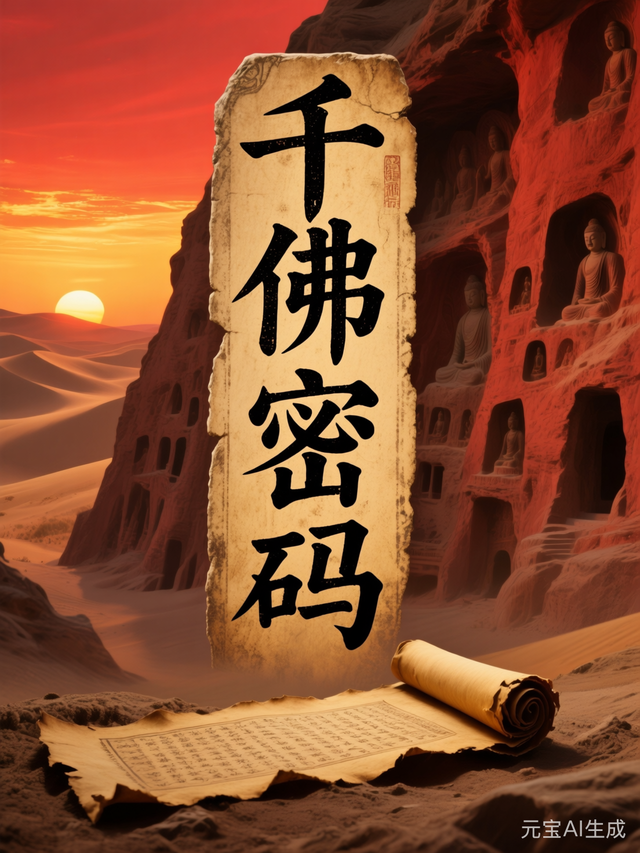
“先生们,”林砚缓缓站起身,将手稿藏在身后,“如果你们想要的是墨家秘宝,恐怕找错人了。”
他突然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大喊:“有人抢劫!”
随后迅速切换成波斯语,向闻声赶来的船员描述“两名男子试图偷窃我的学术资料”。船员们大多是中东人,听不懂英语,却被林砚的方言和急切的神情打动,纷纷围了上来。
两名间谍见状不妙,只好悻悻离去。
林砚靠着门板,冷汗浸湿了衬衫。他意识到,恩师的失踪绝非偶然,墨家秘学背后,牵扯着远比学术争端更为复杂的势力——或许是国家间谍,或许是神秘组织,甚至可能是那个传说中未曾消亡的墨家分支。
而他,一个被学术圈抛弃的“异端”,即将踏入这片充满未知与危险的西域大地,迎接一场关乎知识、信仰与命运的终极探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