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藤花架下的风是软的,裹着暮春的潮气,把徐可卿鬓边的碎发吹得轻轻晃。她低头拂去《新青年》封面上的落瓣,浅紫的花瓣沾着细绒,像极了十六岁那年顾言翻墙时,落在他肩头的玉兰花瓣——那时他手里也攥着这本杂志,油墨香混着玉兰花的清苦,成了她青春里最鲜活的注脚。
指尖摩挲过“劳工神圣”四个字,纸页被翻得有些发脆,是她这些日子反复翻看的缘故。顾言的信还夹在第38页,钢笔字迹力透纸背,“给她们的日子点盏灯”那行,被她用铅笔轻轻描过一遍,墨色叠着铅灰,像两个人的手,悄悄攥在了一起。
她没有直接去夜校。从圣颐女校到北新城东头的旧仓库,要穿过两条窄巷,巷子里满是煤烟味和小贩的吆喝。徐可卿把《新青年》揣进布包,又从包底摸出个粗布小袋——里面是她前夜裁好的生字卡,用的是徐家旧宅剩下的宣纸,她怕太滑,特意用米汤浆过,边角磨得圆润,不会刮到女工们的手。
快到仓库时,远远就看见巷口立着个熟悉的身影。顾言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,袖口卷到小臂,正帮着两个穿短打的汉子搬木板。听见脚步声,他回过头,眼里的笑意像被风吹亮的煤油灯
顾言我还以为你要再等几日。
徐可卿
徐可卿昨夜看了你的信,翻来覆去没睡着,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搭架子。
顾言打开布包,看见那些整整齐齐的生字卡,指尖顿了顿。他抬头时,正撞见徐可卿望着仓库的方向,眼神里没有半分局促,只有一种安静的笃定。仓库的门是破的,用铁丝捆着,里面隐约传来扫灰尘的声音,混着几声低低的笑。
顾言里面是张大姐她们
顾言今早我去工厂找她们,说要教认字,张大姐攥着我的手,指节都在抖——她说这辈子没敢想过,能有一天自己把名字写在纸上。
徐可卿的心轻轻揪了一下。她想起母亲还在时,教她写“忠孝节义”四个字,那时她嫌笔画多,总偷懒画圈
顾言和徐可卿并肩走进仓库,里面已经收拾出一片空地。墙角堆着几个旧木箱,被拼成了课桌,上面摆着顾言找来的煤油灯,玻璃罩子擦得锃亮。三个女工正蹲在地上扫灰,见他们进来,都有些局促地站起来,手里的扫帚还攥着,指缝里沾着黑灰。
顾言这位是徐小姐,以后她跟我一起教大家认字。
说话间,女工们陆续来了,十几个女人挤在小铺里,蓝布衫、灰布衫叠在一起,像一片沉默的海。顾言把油灯往桌子中间挪了挪,拿起一张纸
顾言今天咱们先认‘人’字,一撇一捺,站得端端正正,咱们都是人,都该有认字的权利。
他写字时,手腕稳得很,笔尖在粗糙的纸上划过,留下清晰的痕迹。徐可卿坐在旁边,帮着给女工们递笔,看见张姐握笔的样子,指关节都绷得发白,便轻轻走过去,握着她的手
徐可卿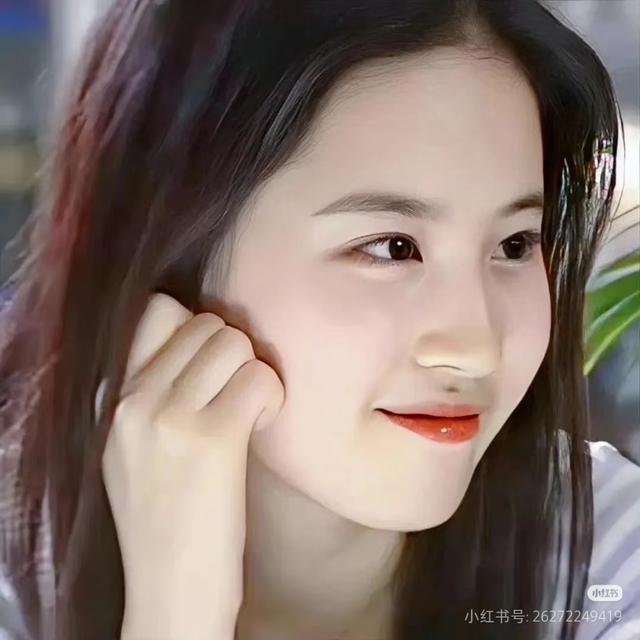
徐可卿张姐,笔要虚握,这样才有力气写。
万能龙套我……我会写‘人’字了?
她抬头时,眼里闪着光,像看见星星似的。徐可卿点点头,心里忽然热起来——这便是顾言想点的灯,是能照进女工们心里的光。
夜深了,女工们陆续走了,张姐走时攥着写满“人”字的纸,像握着宝贝似的
万能龙套徐小姐,顾先生,明天我还来。
女工们均已离开只留下顾言和徐可卿
顾言今天谢谢你
徐可卿抬头,看见他眼里的光,和十六岁那年玉兰树下一样亮。
顾言你还记得玉兰树下吗?
顾言等太平了,我再带你回去看,那时咱们再念《青春》。
徐可卿点点头,风里又传来紫藤花的香气,和那年玉兰树下的墨香混在一起。她知道这乱世难平,知道夜校的灯可能随时会灭,知道他们或许走不到太平的那天,但此刻握着笔的手很稳,身边人的脚步声很坚定,便觉得没什么好怕的。煤油灯的光在地上拖出两道影子,紧紧挨着,像要在这乱世里,拼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。
顾言你回去吧,路上当心。
徐可卿
徐可卿嗯
分开后他们又一次以这样的当时站在一起,但他永远不会知道,她答应帮忙办夜校,不是因为爱情,而是因为在他眼中,她看到了比爱情更重的东西。是纱厂女工裂着厚茧的手攥紧空白纸的茫然,是《新青年》里“为庶民立言”落在心头的分量,是他蹲在杂院矮凳上,一笔一画记女工名字时,煤油灯映在眼底的赤诚。她读了太久李大钊先生的《庶民的胜利》,总想着别只做书里的看客,不是躲在图书馆抄诗,是让那些连自己名字都认不得的人,能握着笔写出“我是谁”,能不再被工头随意欺辱。顾言的脚步,恰好踏在她想走的路上,这份“实实在在为国为民”的心意,比儿女情长更让她觉得踏实,也更值得她去担当。
笃志学社
从昨天看到读书会的告示林杭景就对这个读书会充满兴趣,次日林杭景和成钰特意过来,里面的人正在激烈讨论鲁迅先生发表的《狂人日记》
牧子正猛地站起来,双手按在桌上,声音洪亮。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,眼里闪烁着对革命理想的执着光芒。他刚读完鲁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,心里满是对封建礼教的愤怒和对新社会的向往
牧子正没有行动,那只能成为世人眼中的疯子,敢于付出行动,才是真正推翻封建礼教的革命者
牧子正我们的未来是否繁花似锦,取决于我们当下是否努力
牧子正若只是空喊口号,不付诸行动,那‘自由平等’永远只是镜花水月!
牧子正的观点像一颗石子,在众人心中激起层层涟漪,瞬间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坐在他旁边的成钰眼睛一亮
成钰这位同学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呢
笃志学社社长笑着站起来,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,文质彬彬,目光落在成钰和林杭景身上
笃志学社社长稀客稀客,居然还有圣颐女校的学生来参加
此时林杭景与牧子正四目相对眼里满是欣赏
此时又站起来一个同学语气满是鄙夷
万能龙套圣颐女校?这学校里的学生都是非富即贵,我们谈论的可是新闻学和时政,追求自由平等和公理,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小姐,恐怕是无法理解吧
他的话像一盆冷水,瞬间浇灭了学社里原本热烈的气氛,众人都停下讨论,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林杭景和成钰,等着她们的回应。
林杭景没有生气,只是平静地看着那位同学,语气坚定却温和
林杭景这位同学,既然你提到追求平等自由和公理,那么首先就要打破阶级,不过在你的脑海里早已将人分为三六九等,阶级观念好像特别的顽固呢
她的声音不大,却字字清晰,像一把温柔的剑,字字珠玑
万能龙套我……
笃志学社社长大家都是来辩论的,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来参加,能有更多思想的碰撞,我欢迎圣颐女校的同学
结束后林杭景与牧子正并肩走在路上
林杭景你跟那几位辩论的男生一样、都是大成男校的学生?
牧子正我不是学生
牧子正我平时在我舅舅的风筝铺打工,有空就会去大成离听。所以就认识那些同学
林杭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很不容易呀。
牧子正打工是为了生活,念书是为了获取营养,两者缺一不可。
林杭景说这话时,心里轻轻颤了一下。她想起父亲没出事前,自己也是衣来伸手的大小姐,书房里的书堆得比人高,从不用愁下一顿吃什么。可自从父亲被诬入狱,母亲又走得早,她揣着仅有的行李投奔萧家时,才知道“不容易”三个字有多沉——夜里在煤油灯下缝补旧衣裳,白天要应付学校里的刁难,连买一本新的青年杂志,都要攒好久的零花钱。牧子正说的“打工为了生活,念书为了获取营养”,她比谁都懂。
牧子正杭景、我舅舅的风筝铺就在西二街的第二个路口.你要进去坐坐吗?
林杭景不了、我还有点事。
牧子正那好吧,以后有空的话,欢迎你过来玩。
林杭景好啊
成钰拉着林杭景的手
她一边说,一边挤眉弄眼,显然是在调侃林杭景和牧子正。
成钰杭景,我觉得这个学社,我们以后可得常来,不仅能够学到知识,还能结交很多同学,尤其是借给你橡皮的男同学
林杭景成钰,你说什么呢
成钰我都看到了你还不承认
林杭景你看到什么了?
成钰看到你们眉目传情啊
林杭景成钰……
林杭景假装生气,可心里却没什么波澜——她刚才看牧子正,更多的是一种共情,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,而非别的情愫。
成钰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
成钰不过像牧子正这么细心的男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呢
成钰杭景,你知道吗,他以前还是个大少爷,他爹曾经做过清廷的画师,也算是书香门第,只可惜后来抽鸦片把家给败了,自己又撒手人寰了
林杭景的脚步猛地顿住。风吹过巷口的老槐树,叶子簌簌落下来,落在她的发间。她想起父亲出事时她也是这样,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进泥里,从有父亲疼爱的大小姐,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。牧子正的遭遇,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她曾经的狼狈,也让她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
林杭景你怎么知道这些的?
成钰我是听学社里的男生说的呀
成钰他和他母亲相依为命多年,家里又没法供他念书,所以他得空的时候就去学校旁听,你看到他背的那框风筝了吗?听说全是他自己画的
成钰他爹虽然去世的早,但却把画画的天赋遗传给了他,也算是留给他们母子俩一点吃饭的手艺吧
林杭景没想到他家里还遭受过这样不幸的变故
她轻声说,心里忽然想起了另一个人。
徐光耀出身将门,衣食无忧,却从没有过半点少爷的架子。他知道她的难处,却从不说破,只是默默地帮她,给她送书,帮她解围,甚至在她被人围攻时,站出来护着她
以前她总觉得,她和徐光耀之间隔着云泥之别,他是高高在上的少帅,她是落魄无依的孤女。可此刻听着牧子正的故事,她忽然明白,出身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。就像牧子正,哪怕家道中落,也没放弃读书的念头;就像徐光耀,哪怕身处高位,也没忘记心里的正义。
成钰杭景,你怎么了,发什么楞啊?
林杭景我只是觉得,他很勇敢。
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难,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理想,就像……就像徐光耀那样,在乱世里,始终握着心里的那束光。
她抬手摸了摸布袋里的《狂人日记》,指尖触到书脊上那道浅淡的指痕,忽然想起徐光耀送她这本书时沉声道
徐光耀杭景,这书里的狂人不是真疯,是敢戳破‘吃人’礼教的清醒。往后若遇着让人裹足的黑处,别学那些‘正常人’藏起本心,就像这书教的,守住那点不被同化的劲,就不算输给世道。
风又卷着槐花香来,林杭景望着远处渐亮的天,心里先笃定了几分。可指尖再触到书脊,忽然慌了神
她想着,下次见着他,该说句像样的谢谢吧?
又猛地回神,只当是感激,却没察觉那点心慌里藏着别的。她攥紧书往前走,脚步却慢了半拍,其实她没敢问自己,这份“想再见”,到底是怕辜负嘱托,还是怕,再也见不到他。